读书笔记:浅析余华小说的语言叙述特点
余华,人称当代的先锋派文学的主流人物,他的作品,把人物和情节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中去,以血腥、暴力、淫乱来反映人生的痛苦。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等,近年来又推出新作《文城》。他的作品屡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但由于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与国内文学主流媒体表现方式和内容大相径庭,所以,国内对他的作品颇有微词,国内各种文学奖项也与之无缘。
对他的写作内容,有个人的好恶,姑且不谈。但余华在写作的形式和语言上,确实有他独到之处。他打破了人们常用的传统文字语言运用方式,独出心裁地把过去认为不合语法规则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形成全新的语句,让人读来耳目一新。在叙事结构上,采取时空错位、分裂、语句倒装等手法,让情节呈现多重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
先看几个例子。《在细雨中呼喊》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后来整个下午,村里人看到孙广才在寡妇家中若无其事地喝酒。然而这天半夜村里人听到了来自村外毛骨悚然的哭声。我哥哥听出了那是父亲在母亲坟前的痛哭。我父亲在寡妇睡着以后偷偷来到坟前,悲痛使他忘记了自己是在响亮的哭喊。
这一段的叙事过程,显然和正常的顺序有所不同。一般人的表述顺序用该如下:
1. 整个下午,村里人看到孙广才在寡妇家中若无其事地喝酒。
2. 晚上,我父亲在寡妇睡着以后偷偷来到坟前。
3. 半夜村里人听到了来自村外毛骨悚然的哭声。我哥哥听出了那时父亲在母亲坟前的痛哭。
4. 悲痛使他忘记了自己是在响亮的哭喊。
显然,在这里余华运用了倒装句,造成了语序和时空的错位感觉,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方式。
这种倒装句和时空错位的叙述,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方式,在余华的文章里比比皆是,读来给人异样的感觉。
同时,我又感到他这种语序的形成,应该是长期阅读国外翻译小说的结果,是一种不自觉形成的叙事方式。我们知道,外语的句子结构所修饰语大都放在句子的后面,主、谓、宾语在前,定语、补语、状语等等都在后,这样就造成了翻译的句子,前面说了主要的事件,后面又有几句补充。我们阅读翻译过来的小说,远远没有国内知名作家,用母语写成的书籍读的流畅,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这一句,更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子:
父亲呜咽着走回寡妇家中,他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犹犹豫豫。
按照通畅的中文写法应该是:父亲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犹犹豫豫,他呜咽着走回寡妇家中。
余华承认,他的文学启迪与修养,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外名著的滋养,那些翻译过来的作品,明显的有语句倒装和拖拉说明的痕迹。长期的阅读和默化,就形成了余华的这种文字叙事风格。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语言文字的超常规应用,拓宽了余华文字表达的感染力。比如:“孙广才是由他无限热爱的酒带入坟墓的。”词语“无限热爱”用在酒上,超出了常人的用法,如果小学生用词造句,老师肯定通不过,最起码是不恰当。但余华用在这里,拓宽了词语的含义,兼有嘲讽的意思,也让读者为之一新。
这样例子不胜枚举:“由于酒的鼓励,我父亲像一个少年看到恋人飘散的头发一样神采飞扬。”这里的“鼓励”一词用在酒上,也是别出心裁。
余华的语言风格,充满了诙谐,幽默,而且处处又显示出讥讽和调侃,有时又给人玩世不恭的感觉。他把那些本来血腥、死亡和恐怖,以及荒诞离奇的情节,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显示出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让人惊叹不愧为先锋派大师。看下面这段例子:
孙广才落入粪池淹死,喝醉了酒的罗老头晚上以为遇到了淹死的猪,刚要喊“谁家的猪掉...”,马上自己捂住了嘴,等他拽上来看清楚是孙广才,一脚蹬回粪池,嘴里骂道:“他娘的,你死了还要捉弄我。”
本来看到淹死人是件恐怖的事情,但在余华的文字下,变成了调侃和幽默。对生死亦如此,这不也透露出作者居高临下,玩世不恭的态度么?
至于说道余华小说情节的荒诞和色情,更是超出常人之想象。
他的父亲半个月外出没有回家,一回来就把在地里干活的母亲拽回村里,在别人家找了一条板凳,父亲为母亲解不开裤腰带而大发脾气。“母亲温顺地躺倒,将一条腿拔出来搁在秋天的空气里。”“几只鸡喔喔叫着满怀热情地也想加入其中,它们似乎是不满意孙广才独吞”。
丰富的想象和语言运用,只能让人叹为观止,拍手叫绝。
这样的例子充满全篇,不能不佩服余华的文字功底和情节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一环紧扣一环,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引人入胜。
当然,有些描写太过于露骨和荒诞,让有传统思想的难以接受,显得不近情理和远离现实。但也有评论家说这正是余华的过人之处。
余华出生于1960年,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运动和动乱中度过的。他没有考上大学,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学学习和培养,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和悟性,硬是从一个小镇卫生院的牙医,登上了小说家的舞台,而且出手不凡,一鸣惊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的早期小说,就以刻画苦难世界中,人们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异化的双重压迫下,呈现出贫困与饥饿、暴力与死亡交织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欲望、罪恶、荒诞等情节让人耳目一新,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在学习西方文学大师的创作手法上取得了成功,稳坐了国内先锋派小说家的头牌交椅。
余华虽然出生在浙江杭州,但其父辈却与我是同乡,祖籍是山东聊城高唐人氏。在他的一片散文中,他叙述了当年父亲带他从南方回到山东高唐老家情景:鲁西北的盐碱地,破草房,贫瘠的土地和忠厚的老乡,北方冬季的枯枝败叶和寒冷,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唐老家的姑姑家,亲人包饺子给他吃,余华清楚地记得饺子咸的要命,父亲告诉余华,这是让他把饺子当配菜吃的。更有甚者,在他的新作《文城》里,文章的后半段北方军阀南下,带兵的连长就是山东聊城人,而且会说一口山东快书。可见父辈家乡观念对他创作影响之深。读余华的作品,从中也可以看到许多侠肝义胆的豪杰之士,在人们危难之中慷慨以助,显示着北方人的豪气和勇猛。特别是《文城》中的主人公林祥福的性格,勤劳、善良、更是山东人秉性的真实写照,也应该是余华作为山东祖籍作家的灵魂深处的使然吧。
当然,余华作品中有许多血腥、死亡、性暴露和荒诞的描写,让我们这一代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难以接受,特别是看到外国评论家取其一而抹黑我们国家的现实,也感到很是愤慨。所以,读余华的作品,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语言特色和文学表现技巧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从这点意义上来讲,余华的作品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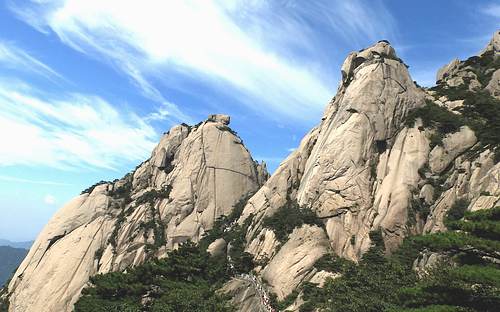
我是推理小说作家呼延云,关于推理小说创作、明清古代笔记中的奇闻异事,问我吧!
在我国古代浩繁卷帙的笔记小说中,记载有大量的奇案、诡案、悬案,古人常常以“鬼怪灵异”作解。然而,诡非鬼,机巧万端终有解;谜莫迷,阅尽千帆道寻常。这些奇案、诡案如何用科学推理的方式来解读? 我是推理小说作家呼延云,近两年,我在文学创作之余,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古代笔记的分类和重构上,并从“对古代谜案的现代解读”这一角度切入,创作了近百篇“叙诡笔记”。用现代科学结合历史考据,给古代笔记小说中的奇案、诡案、悬案做出全新的合理解释。 古代笔记中有哪些奇案、谜案?它们的真相是什么?关于明清古代笔记小说中的奇闻异事,以及推理小说创作等相关问题,欢迎大家一起聊聊!
叙诡笔记|古人养犬:既不滥杀,亦不滥爱
王安忆论小说(王安忆小说理论笔记)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生活失去了形式,我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文学”(卡尔维诺)
现实世界因为缺乏形式,无法将潜在的意义呈现出来,而文学则可能赋予现实形式,这也就是文学的任务。
我们生活中的形象多如牛毛,而且它们通过乘方,通过万花筒中镜子的反光,还在无休止地增加。大部分这种形,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意义上说,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不会衍生新的意义,不会引起我们注意。(卡尔维诺)
时间在叙述中,是更容易被压缩的。因为叙述总是择其重要,艺术本来的用心与功能大概就是将现实中冗长的时间,规划成有意义的形式,规划的过程中便将无用的时间淘汰过滤小说的时间可以是一瞬间成几世几劫,亦可以几世几劫成一瞬间,是由时间里的价值而定,价值是可摆脱自然的规定,重新来选择排序和进度,将散漫的现实规划成特定形式,这价值也就是卡尔维诺说的“意义”。
当我们决定去描述一个空间的时候,大概提前就要想好,究竟它意味着什么。空间惟有生发含义,才能进入叙述,或者说,我们必须以叙述赋予空间含义,才能使它变形到可以在时间的方式上存在。要在空间里实现主观性,最好的途径是赋予人的气息
倘若留意,我们会发现,四处都是这样的特殊性格的人,但也还是那句话,缺乏一个形式,将这些只鳞片爪组织起来,呈现出意义。现实的力量太强大了,将人的形态全规划为类型,就好像用模具拖出来的一样,那些独一份的特质有时会以疾病的方式苟存着。
现实世界被夯得越来越结实,异质人物只能夹缝中求生存。
小说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生活。
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
“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
优雅在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
唐娜的讲述同样流露出强烈的自恋,沉溺在假想的自我中,很难让她转移注意力,稍稍在他人身上停留一会儿。
性格,是我们小说大有可为的地方。我们队交代动态性的情节可说是弱势。但将行动化为性格便左右逢源,处处开花。
好的畅销书真的走向严肃性,在任何类型里最好的都是艺术,一定是艺术。
情节是有纪律的,年青人喜欢破除常规,一旦破除却会发现事物不存在,因为没有形式了,从某种角度说,常规就是形式。曾经有一次和一个法国教师讨论左撇子, 我说:“我到法国看到很多小孩都用左手写字, 也挺好,在我们中国的话,如果孩子是左撇子,大人三打四骂也得把他矫正过来,就得用右手,在你们这儿却并不在意,爱用哪只手就用哪只手。”那老师说还是应该用右手,还是用右手好,我就问为什么,她想了很久,然后说:“因为写字的方式是为用右手写字的人而设计的。”我一想她讲得太对了,你想尤其是英语,是从左向右写,如果用左手的话,一边写一边就把字擦掉了。所以书写方式就是为右手写字的人设计的。有一些定律我们不能够太对它质疑, 因为规则在起源时就被考虑为条件了,小说要有故事有情节,其实也就是为了最初的需要而决定的。
怎么推进?就是制造矛盾,要给它制造困难,有了困难需要克服,事态才可能发展,制造困难也要按照生活的定律去制造。
现在小说越来越难写,故事不容易编制,就和我们生活中的规矩越来越少有关系。
我就觉得好的作家是从日常的定理出发,但他最后达到的境界是超现实。差一等的则是一开始不守纪律结果又回到纪律上了。我觉得应该先遵守纪律再走出纪律,这就是情节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创作的目的。小说需要策划,策划是有目的,是从真是走到不真实,在现实中的不可能,在理论上却是可能的。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理论上成立,可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也不要求实现。
事物一旦进入语言,一定是先后顺序,不可能并列进入,无论这一件事物拥有多少同时并进的要素,也必得排出一二三四,你的主动性只在于把你觉得应该先说的地方先说,应该后说的地方后说。不管怎样,在形态上表现的就是先后次序。
虚构是偏离,甚至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而存在,它比现实生活更有可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建构为独立王国。生活南面是残缺的,它需要在较长较大的周期内起承转合,完成结局。所以当我们处在局部,面临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没头没尾,而虚构却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够重建生活的状态。
在这个阶段中,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古怪,不合时宜,我为他们命名为“浪漫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基本是由坏孩子组成,他们行踪诡秘,心怀叵测,潜藏着犯罪倾向, 这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惯常受到驱逐和排斥。所以说,他们大多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所幸是小孩子,再出格也成不了气候。他们生活在大人的辖制底下,大人的世界是一个合法世界,掌握不可抗拒的法则,他们究竟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他们的行为就有了一种哀戚,也就是说,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他们身体里骚动着莫名的渴望,精力无限充沛,比起《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的剑,还有逃荒的书来,他们身处更为现实的社会里,他们所受的制约更为具体,失败也就更确定无疑。但又因为是些小孩子, 无论行动还是失败就都带有游戏的性质, 这游戏表面似乎是拷贝了大人世界的活动,但我以为苏童无意影射现实,更可能别有用心,就是将现实变形,变形到一个新的存在产生。态度的郑重大大超过应该有的程度, 事情就在夸张中变形,邻里纠纷升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结果是同归于尽。
苏童笔下的坏孩子,都是一个人的黑帮,单枪匹马,孤独地施行犯罪。
乡下里人受得了苦,城里人受得了罪。这受罪不止是身体实际上的付出,还更指心理上的承受。
在一个利益社会里,每一件存在都是以交换的实用性为价值,姚美琴的美貌也纳入了这个体系。
值得出轨,就是说,对得起她的道德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