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
本书对1930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家茅盾、老舍和沈从文做出了精辟研究。
茅盾和革命,对一代革命者的献身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有着深刻体验;
老合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
沈从文则刻意借着城邦与乡村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敞论》、《众声喧哗:三O与八O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围: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后遗民写作》、《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Ficti...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敞论》、《众声喧哗:三O与八O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围: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后遗民写作》、《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m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2004年获选为中研院第25届院士。200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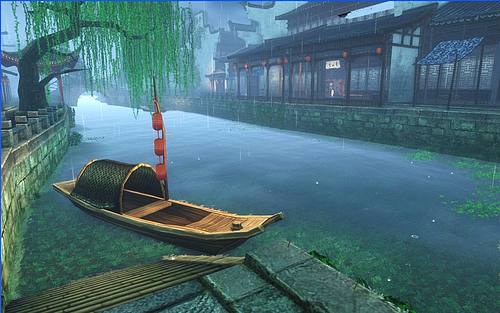
人生派写实小说
人生派写实小说 : 文学研究会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化宗旨和启蒙主义精神,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强调作品的思想和社会价值。反对将文学当做封建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消遣的工具,反对所谓纯艺术的文学,被人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其作品往往围绕如何建设健全的社会、成就理想的人生,以国民性改造、青年恋爱、婚姻、妇女贞洁、人生的目的意义、教育、儿童、劳工、军阀混战等诸多社会和人生问题为题材,揭示社会的黑暗,诅咒灰色的人生,并力图通过小说写作为社会“开药方”。在创作方法上往往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了自然主义。代表性作品有叶绍钧的《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及长篇小说《倪焕之》,王统照的小说集《春雨之夜》和长篇小说《一叶》,王任叔的小说集《破屋》等。
文学研究会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化宗旨和启蒙主义精神,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强调作品的思想和社会价值。反对将文学当做封建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消遣的工具,反对所谓纯艺术的文学,被人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
其作品往往围绕如何建设健全的社会、成就理想的人生,以国民性改造、青年恋爱、婚姻、妇女贞洁、人生的目的意义、教育、儿童、劳工、军阀混战等诸多社会和人生问题为题材,揭示社会的黑暗,诅咒灰色的人生,并力图通过小说写作为社会“开药方”。在创作方法上往往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了自然主义。
代表性作品有叶绍钧的《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及长篇小说《倪焕之》,王统照的小说集《春雨之夜》和长篇小说《一叶》,王任叔的小说集《破屋》等。
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是日本平安中期着名女作家紫式部(本姓藤,原名字不详,978-1015)创作的《源氏物语》,成书于11世纪初。全书共54回,近百万字。小说故事历经四朝天皇,长达70多年,人物共有400余人。小说通过主人公源氏生..
新写实主义 : 1987年,在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派实验小说和文化寻根派小说鼎立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小说倾向。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直面生活、参与现实的精神,但不同的是,更注意吸收纪实小..
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
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发生于1988年前后,但其作为一种小说潮流被正式命名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却源自于《钟山》1989年第3期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写实小说”的特色在于:(1)其创作方法虽然“仍是以..
《新写实绘画》:王林等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7月版。5万字。精选新写实代表作168幅。配以文字,从写实绘画源流说起,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1979-1988年新写实绘画的面貌,梳理了这一重要流派的发展脉络,从中可见社会意识的自觉、..
《论西方写实绘画》:吴甲丰着。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5月版。22.5万字。系统研究西方写实绘画的学术专着。作者以摄影术为主要参照系,以视知觉心理学为主要理论依据,探讨了西方写实绘画的一系列问题。全书共3篇。“上篇”..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200年前,法国作家司汤达曾有言:“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小说与镜子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浩的作品也莫能例外,他的代表作之一《镜子里的父亲》开宗明义,凸现出镜子在其庞杂的叙述框架中的枢轴功用。游览全书,不难发现,它围绕父亲大半生的经历及其家庭成员,以多声部的方式展现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纷繁诡谲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而他早先的那部长篇《如归旅店》里的中心人物还是那个不服输、竭力维护一己尊严的父亲,只不过作者将时代背景挪移至上世纪前半期。如果从最平常的意义来理解小说与镜子的关系,那么这类小说在当代文学书写中可谓汗牛充栋,横跨长时段的史诗性视野与气魄,细腻真切的人物描绘和风俗画面,加上对历史事变或深刻或浮浅的反思,构成了这类写实小说的基本特征。赢得批评家和读者双重喝彩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就素材而言,李浩完全可以依照这一为人耳熟能详的模式,敷衍出诸多清晰精准的篇章。但他偏偏走上了一条迷蒙不明的异路。
李浩笔下的镜子,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祛除了种种偏见的媒介,它并没有忠实无欺地将大千世界一览无余地折射而出;相反,它本身便可成为人们质疑盘诘的对象。显而易见,作者并没有将它固定地矗立在大地某处,它有时居高临下,有时匍匐在地,有时侧转、扭动,而在上面飘掠而过的是一组组影像,变动不居,或斑斓浓艳或单调暗淡,而父亲一生中的重大关节点、颇富戏剧性的场面一一悉数映现。叙述者执着地探寻着父亲生命的意义,触摸着它与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间难解难分的纠葛。
童年的艰窘、成长的困厄、亲人间温暖而又令人窒息的粘连,不无荒诞意味的历史大潮中个人的随波逐流,种种怪诞发噱的细节(最鲜明的莫过于爷爷几次表演性十足的自杀),打上时代烙印的恋爱婚姻,几代人的生老病死被作者镶嵌在母语般熟稔的乡村生活的背景中。尽管它们并没有依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展示,但散缀在全书各处的众多炫目的碎片最终还是汇聚合成了一幅宏伟的画面,流溢出史诗般的韵味。
李浩笔下的父亲,就其个性特征而言,还不足以成为哈姆莱特、堂·吉诃德或阿Q式的人物。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无缘,他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怯懦、隐忍,历经坎坷磨难,屡遭败绩,终其一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但他苦苦撑持,死抱着最后一丝尊严和脸面,这也是父亲一世为人的价值之所系。这样的人物在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并不罕见,但李浩笔下的父亲之所以能感染我们,靠的不是传奇性的秘闻野史,而是作品内蕴的风格的力量。
与大量平庸、表达过于顺畅的作品相比,李浩的文本体现出他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他曾明确表示不想写任何“已知”的小说,而这正鲜明地体现了先锋文学的前卫精神。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小说一度异军突起,改写、重塑了当代文学的版图。但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它便趋于式微,而故事性强、贴近现实生活、文笔流畅的作品又一次成为文坛的霸主,人们还美其名曰“好看的小说”,似乎认定小说从来就是、现在便是、未来也将是这类作品。毋庸讳言,它们给人极强的阅读愉悦,但在艺术形式、语言风格方面的创新上却乏善可陈,只是沿袭了前人行之有效的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小说艺术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正是在这点上,李浩将自己和大量沉醉在写“好看小说”的同行拉开了距离,他不想成为一个单纯讲述故事的艺人,而是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将小说真正作为一门艺术来打磨,在未知的畛域中开拓出新的天地。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先锋姿态使李浩处于与读者的紧张关系之中,不少人指责他自高自大,忽视读者的感受。和那些印数惊人、低三下四地迎合读者的作品相比,李浩卓尔不群的文字无疑会惹恼相当数量的读者,但他对艺术品质坚持不懈的坚守和追求,使当代文学的先锋精神不至于湮没灭迹,为同时代也为后代树立了一个醒目的标杆。

